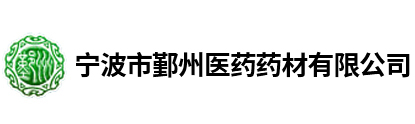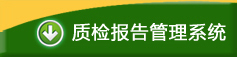醫藥云端信息:挖掘趨勢中的價值
文 | 陳昊
作者: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藥品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 陳昊
目前����,上海市2016年5院6區藥品GPO(集團采購組織)采購項目正緊鑼密鼓推進實施�,首批覆蓋150個抗生素和心血管藥品���,第二批400個藥品以及第三批GPO采購目錄內剩余其他藥品也將在1~2個月內完成采購�����。同時���,重慶本年度23個短缺藥品的供應保障也會采用GPO采購形式。
省級雙信封入圍�、地市醫療機構聯合帶量采購(GPO)
據了解����,全國包括深圳在內多個地區擬在2016年內全面啟動以GPO作為帶量采購的實現形式���。一時間地市級醫療機構聯合采購和GPO成為業內炙手可熱的名詞����。
去年,全國各省陸續啟動了新一輪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經過數月的探索�,安徽、福建已完成2015年標期采購�����,浙江���、江蘇�、天津等省市正式展開在地市層面的帶量采購。隨著2015年11月最后一批的13個省聯入國家藥管平臺����,全國范圍內已初步形成如下格局: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平臺演變為技術質量標準入�����、省級限價入圍性質,地市層面醫療機構聯合體帶量采購(GPO)產生藥品最終成交價格�。
雖然迄今僅有不足十個省市在按照上述方式推進省級藥品集中采購�,更多的省市依舊處于觀望態勢��,但已實施采購地區的探索實踐已足以成為眾多省份著手實施下一階段藥品采購計劃的政策參考�。2016年4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醫改試點地區擴大至200個地市和8個省份���,意味著依照“省級雙信封入圍�����、地市醫療機構聯合帶量采購(GPO)”方式實施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將正式成為主流形式�����。
醫保改革滯后,藥采仍陷“以藥補醫”
由于2015年密集出臺的深化醫改政策均強調新一輪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應在三醫聯動的綜合改革措施下施行���,鑒于醫保基金已經成為我國醫療衛生費用的主要支付者����,因此��,藥品醫保支付標準政策的出臺理應成為實施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方式改革的配套條件。
如果缺乏醫保支付方式的相應調整�,必然會影響公立醫院參與藥品集中采購方式改革的積極性��,為建立正常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為改革重要目標的醫改深入帶來困難。然而���,繼2015年9月人社部門發布《關于印發基本保險藥品支付標準制定規則(試行)的通知》(征求意見稿)至今,仍未有正式文件出臺�����,藥品醫保支付標準調整的國家級指導性文件的頒布實施嚴重滯后于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方式改革進程����。
改革先行地區安徽在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及安徽省增補目錄的基礎上制定了基本用藥目錄(覆蓋1118個品種,涉及4141個品規)并將其確定為醫保支付范圍�����,將2015年省級集中采購入圍價則作為第一輪的藥品醫保支付標準及零售價格���、實行零差率的前提下�,實施“16+1”單元地市及省直醫療機構聯合體藥品帶量采購�。醫療機構直接獲取藥品醫保支付標準與各帶量采購單元實際成交價的差額作為取消藥品價格加成的收入補償。
受此直接獲取降價收益的激勵�����,安徽省2015年藥品集中采購實際成交價格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破除了藥品價格虛高的不正?��,F象�����。然而,安徽的帶量采購、醫療機構直接獲取議價收益所得的激勵方式被企業�、媒體和專家廣泛詬病為“隱蔽形式”的以藥養醫和忽視質量風險��、唯低價是取的“二次議價”,讓安徽省后續的綜合改革陷入輿論被動。
有鑒于此��,其后浙江省在制定相關改革方案時���,同樣采取將本輪省級藥品集中采購的入圍價作為首輪藥品醫保支付標準����,對于試點的寧波、溫州、紹興等地區帶量采購形成的實際成交價與藥品醫保支付標準之間的議價所得差額�,則采取上繳財政��、再通過對醫療機構特定方式的考核之后予以返還處理�。浙江式的議價收益處置避免了形式上的“以藥補醫”,同時將這筆收益轉變“身份”變為財政對辦醫事業的直接投入���,似乎在道義上取得了成功。
同期,上海則在部分試點區縣和醫療機構集團內實施藥品GPO采購����,要求參與GPO采購項目的藥品生產企業在報價時主動承擔“物流分攤比例”�����,并將“分攤比例”考核后返還醫療機構作為鼓勵其參與藥品采購改革的激勵因素�。上海的藥品GPO采購方式由于使企業議價讓利披上了“供應鏈優化”��、“藥品服務價值延伸”的技術外衣而更加師出有名�����,一時為全國各地所關注并可能陸續大范圍跟進。
可見,不管采取哪種形式,通過“帶量采購”名義實現的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入圍價與醫療機構帶量采購實際成交價之間的所謂“二次議價”收益��,都被視作了鼓勵醫療機構積極參與以“降低藥品虛高價格�、破除以藥養醫”為目標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方式改革的激勵因素。
然而,不論哪種形式去處理這部分“議價收益”�,都未能改變其深層次仍然是變相的“以藥補醫”本質�����,這正是本輪深化醫改采取將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方式作為“騰籠換鳥式”改革切入點所面臨的最大的理論困境。
同時,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在地市帶量采購層面能夠比省級入圍實現更大幅度的降價�,一方面是不是表明�����,我們現行省級藥品集中采購方案里的質量技術與價格入圍仍存在降價效力不突出的機制性疑問?另一方面,是不是表明由醫療機構聯合體去執行帶量采購����,能更有效率地去發現藥品的真實價格?

▲4月17日在上海舉辦的“居危謀變群英會”上陳昊做GPO主題演講
改革有“窗口期”����,不動則已��,一動全動
改革的本質是利益重新調整和合理地再次分配,任何改革都無法顧全所有的利益方而只能去追求社會總體價值的最大化���。基于這樣的認識��,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方式的改革既然承擔起了切入深化綜合醫改的歷史性責任����,如何在追求程序正義的前提下以爭議最小的方式去實現“四個有利于”的改革目標,應該是政策設計者應優先考慮的問題����。
藥品和藥品質量的特殊性使得藥品行業具備相當程度上無法壓縮的剛性成本����,這也決定了必然有一個保障藥品質量和服務所必需的藥品價格平衡點�����,藥品價格不可能無限壓縮��。
換言之,降低藥品價格虛高�、取得騰籠換鳥的改革空間�,既有空間大小制約改革力度的問題����,也有如何抓住有限的降價次數和降價幅度所帶來的及時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推進綜合醫改前行這一寶貴的改革“窗口期”的問題��。
這也是為何多數省份在面對有關部委要求各省自2015年11月必須全面啟動省級公立醫院藥品采購����,但迄今實際進度依然非常緩慢的重要原因���。面對整體設計�、三醫聯動的深化醫改,必須謹慎行事��、各項措施全面聯動���,改革不動則已���、一動全動��。否則�,錯失寶貴的全面調整的”窗口期“,會為后續改革的推進帶來極大的難度和高昂的社會成本�����、時間成本����。
對于各省如何繼續推進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制度的完善、為深化醫改探索出一條更符合社會總體利益提升的道路�����,我們仍需要作出理論上的再設計并審慎地進行推進實踐,各方也難免繼續承受改革轉型期所帶來的沖擊與陣痛�����。
信息來源:醫藥云端信息